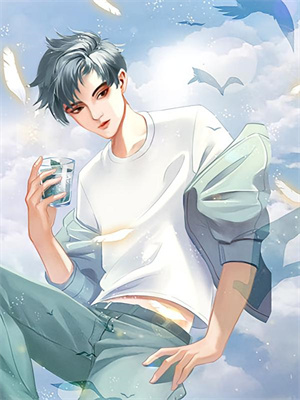简介
《溪隐龙兴汉》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历史古代小说,作者“西门一刀”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描绘,为读者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。小说的主角刘秀勇敢、善良、聪明,深受读者们的喜爱。目前,这本小说已经更新总字数213879字,喜欢历史古代小说的你快来一读为快吧!
溪隐龙兴汉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建平八年的冬天,济阳比往年更冷些。官舍后院的老槐树叶子早已落尽,光秃秃的枝桠伸向铅灰色的天空,像一双双干枯的手。前堂的灯从黄昏就亮着,青铜油灯的光昏黄摇曳,映得案上的 “济阳令印” 泛着冷光 —— 这枚铜印,再也不会被它的主人刘钦握在手中了。
刘秀跪在灵前的蒲团上,身上穿着粗麻布丧服。东汉时官员丧仪有定规,子为父服 “斩衰”,丧服需用最粗的生麻布,不缝边,以示哀痛。麻布粗糙的纹理磨着皮肤,刺得人发痒,可刘秀却一动不动,只有肩膀偶尔微微起伏 —— 他已经九岁了,比三年前又高了半头,眉眼间褪去了孩童的稚气,多了几分沉稳,只是此刻,那双总含着温和的眼睛,盛满了泪水,却强忍着不让它落下。
灵柩停在前堂中央,是用本地的老榆木做的,没有刷漆,保持着木头的原色,只在棺沿系了三根麻绳,供亲友扶棺。棺前摆着一张矮桌,桌上放着刘钦的灵位 —— 用柏木做的,上面用隶书刻着 “济阳令刘公讳钦之位”,灵位前的陶碗里,盛着半碗粟米粥,是樊氏亲手煮的,还冒着淡淡的热气,却再也等不到它的主人。
樊氏坐在灵柩旁的矮凳上,穿着与刘秀同款的粗麻布丧服,头发用一根白麻绳束着,脸色苍白得像纸。她的眼睛红肿不堪,泪水无声地落在衣襟上,晕开一片片深色的痕迹。春桃站在她身后,手里拿着一块粗布帕子,不时递过去,却不敢多说话 —— 东汉时女子居丧需 “静哀”,不可喧哗,春桃虽只是丫鬟,却也懂这规矩。
门房老周端着一碗热汤走进来,轻轻放在刘秀身边的地上:“小郎君,喝口汤暖暖身子吧,你已经跪了大半天了。” 老周的声音沙哑,眼睛也红红的 —— 刘钦待他不薄,去年他家乡遭灾,还是刘钦给了他粮食,让他能养活家人。刘秀摇摇头,目光依旧落在灵柩上,声音带着哭腔,却很轻:“我不饿,爹还没回来呢。”
“爹回不来了……” 樊氏的声音哽咽着,打断了刘秀的话。她伸出手,想摸摸刘秀的头,却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。刘秀转过头,看着母亲苍白的脸,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。他想起昨天晚上,父亲还在灯下教他读《尚书》,指着 “允恭克让” 四个字,说 “做人要像溪水一样,温和却有力量”,可今天,父亲就永远地离开了他。
就在这时,窗外突然闪过一道白光,紧接着,“轰隆” 一声闷雷响起 —— 冬天打雷本就罕见,这雷声却格外响,震得窗棂都微微颤动。老周跑到门口一看,惊呼道:“流星!有流星坠进后溪了!” 樊氏和刘秀也抬起头,往窗外看去,只见后溪的方向,一道红光划过夜空,像一团火,直直地坠进溪水里,紧接着,就听见溪水传来 “呜咽” 般的声音,像是在哭泣。
“这是…… 不祥之兆啊。” 前来吊唁的张老丈拄着枣木杖,颤巍巍地说,“刘令君是好官,怎么会有这样的异象……” 其他亲友也纷纷议论起来,有的说 “流星坠溪,怕是济阳要有灾祸”,有的说 “刘令君英灵不昧,这是在警示我们”,场面顿时有些混乱。
樊氏听到议论,身子晃了晃,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。刘秀赶紧扶住母亲,就在他的手触到母亲手臂的那一刻,掌心突然传来一阵温热 —— 是那道伴随他长大的龙形温痕!之前这痕迹只是偶尔会暖,可今天,却像被火烤过一样,烫得他指尖发麻。他能清晰地感觉到,一股温和却坚定的力量从掌心蔓延开来,顺着手臂流遍全身,原本沉重的身体突然轻松了些,心里的悲恸也似乎被这股力量抚平了几分。
“娘,别怕。” 刘秀的声音比刚才沉稳了些,他扶着樊氏坐稳,“爹没有离开我们,他在保护我们呢。” 樊氏疑惑地看着他,刘秀抬起手,掌心的龙痕虽然看不见,却能感觉到温度。“您看,” 刘秀把掌心贴在母亲的额头上,“爹的气息还在,这龙痕就是爹给我们的念想,他会一直护着我们的。”
樊氏触到刘秀掌心的温度,心里忽然安定了些。她想起刘钦生前常说 “秀儿有天命”,想起赤光临舍、九穗禾的异象,想起黄石翁的 “溪隐待时”,眼泪又流了下来,却不再是绝望的哭,而是带着希望的缅怀。“是啊,你爹还在,他还在护着我们……”
窗外的雷声渐渐停了,溪水的呜咽声也轻了下去,只有青铜油灯的光,还在静静映着灵柩。刘秀重新跪回蒲团上,掌心的龙痕依旧温热,像父亲的手,轻轻覆在他的手上。他看着灵柩,在心里默默说:“爹,您放心,我会照顾好娘,会好好读书,好好学本事,将来像您一样,做个保护百姓的好官,不辜负您的期望。”
夜深了,亲友们陆续散去,只留下樊氏、刘秀和春桃守灵。春桃煮了些粟米粥,樊氏勉强喝了半碗,刘秀却一口没动,只是跪在灵前,睁着眼睛,看着灵柩,仿佛这样就能等到父亲回来。天快亮的时候,刘秀实在撑不住,趴在灵前睡着了,梦里,他看见父亲站在后溪畔,对着他笑,手里还拿着那卷《尚书》,说 “秀儿,要记住‘民为邦本’,不要忘了溪畔的初心”。
第二天清晨,刘钦的友人邓先生带着几个南阳同乡赶来吊唁。邓先生穿着素色的曲裾深衣,腰间系着白麻绳,这是东汉时友人吊丧的 “吊服”。他走到灵前,对着灵柩深深鞠了三躬,然后对樊氏说:“樊夫人,刘贤弟走得突然,南阳的族人已经知道了,让我来接你们回舂陵(chōng líng),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樊氏点点头,泪水又流了下来:“有劳邓兄了,只是…… 钦儿的灵柩,我想带回舂陵安葬,让他魂归故里。” 邓先生说:“夫人放心,我们已经安排好了车马,会小心护送刘贤弟的灵柩回舂陵。”
刘秀听到 “舂陵”,心里一动。舂陵是刘氏的祖籍,也是母亲的家乡,他还想起,邓先生之前说过,新野离舂陵不远,等回到舂陵,说不定就能见到阴丽华小姐姐了。他摸了摸怀里的圆石,圆石暖暖的,和掌心的龙痕一样,像是在为他鼓劲。
接下来的几天,亲友们帮着料理刘钦的后事。按照东汉的丧葬习俗,他们在官舍外搭了灵棚,供村民吊唁,刘钦生前帮助过的百姓,都带着粟米、布帛来祭奠,有的老人还哭着说 “刘令君是好官,怎么就走了呢”。刘秀每天都在灵棚里接待吊唁的人,虽然年纪小,却做得有模有样,递茶、还礼,言行举止都透着沉稳,让亲友们暗暗称赞 “刘令君后继有人”。
出殡那天,天阴沉沉的,刮着冷风。灵柩被抬上牛车,牛车是用犍牛拉的,车辕上系着白麻布,后面跟着长长的送葬队伍,亲友们穿着丧服,手里拿着哭丧棒,慢慢往城外走去。刘秀走在灵柩旁,手里捧着父亲的灵位,掌心的龙痕一直温热,他知道,父亲在看着他,在陪着他回家。
走到后溪畔时,刘秀忽然停下脚步,对着溪水深深鞠了一躬。他想起在这里读书、洗衣、劝和顽童,想起父亲带他来这里教他 “溪隐待时”,想起黄石翁的青衫身影。“爹,我们要走了,以后我会回来看看的。” 溪水轻轻流淌,像是在回应他的话。
送葬队伍继续往前走,刘秀回头望了一眼济阳官舍,望了一眼后溪,心里暗暗说:“济阳,我还会回来的。” 他不知道,这次离开,不仅是回到祖籍,更是他 “溪隐待时” 的新起点,在舂陵的白水溪畔,还有更多的考验和机遇在等着他,还有那个让他心心念念的阴丽华,在不远的未来等着与他相遇。